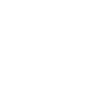这个文章将对大家想知道的理群、洪子诚、吴晓东等“再谈文学性”诗学、历史与人和对疫情的看法采访对话稿的题进行详细解,希望对各位网友们有所帮助。
“文学是人类研究的说法可能永远不会过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在2022年8月21日举办的“重谈文学性诗学、历史与人文”工作坊上总结了关于文学性的核心话题。本次工作坊以吴晓东教授的新书《文本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为切入点,试图对当今学术界与“文学性”相关的诸多经典题进行更加深入、多元的思考和讨论。语境。诗学、历史、人性维度在“文学”领域的交织、互动与共鸣。
车间现场
研讨会在中央美术馆成功举办。出席研讨会的嘉宾有洪子成、立群、黄子平、吴晓东、倪文健、毛健、江涛、张莉、卢英华、倪永娟、王小平、金力、李国华、袁一丹、李松瑞,李玉阳。
首先,主持人李玉阳简要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由来和目的。李玉阳指出,此次工作坊之所以命名为“再论文学性”,是源于洪子成与吴晓东在2013年进行的题为“文学性经典与阐释”的对话,对话手稿也被收录作为序言。着有《文本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一书。两位老师的对话触及了很多今天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空间的文学性相关题,与会的所有学者也都对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鉴于此,本次研讨会决定以吴晓东教授的新书为基础,邀请老师们就文学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吴晓东,《文本内外现代题材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中央美术馆馆长卢英华、商务印书馆文史编辑室主任倪永娟分别致辞。卢英华对老师们新书的出版表示诚挚的祝贺,邀请嘉宾参观中央美术馆策划的新展《宽阔写实之路——1920-1980年代摄影的人文实践》,并感谢中央美术馆馆长与中级艺术基金会的合作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倪永娟表示,很荣幸担任《文本的内与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的主编。在编辑过程中,研究员诗意温柔的文字和文本分析让她在阔别校园多年后再次真切感受到文学的熏陶。称呼。对于“文内与文外”的话题,倪永娟认为,年轻学生可能更容易感受到“文内”,但对“文外”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进入职场后,粗糙的现实或许促进了读者对“文外”的认识和理解,但与此同时,“文内”的感受可能正在慢慢变得淡漠。因此,阅读这种兼顾文本内外的文学研究著作,并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场滋养心灵的文字之旅。对此,吴晓东在与洪子成的对话中表示,“赋予文学一些深刻内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倪永娟指出,当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我们或许应该继续,那种曾经引领我们表达、呼喊的文学,是否还承载着人们厚重而丰富的情感?次?曾经拓展我们想象和经验边界的文学还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想象和体验吗?曾经抚慰人心的文学是否还能帮助人们回归内心的平静与充实,这或许也是本次工作坊关注的一个重要题。
工作坊第一环节是立群、洪子成、黄子平、吴晓东四位老师的对话。首先,立群老师做了题为《疫情期间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演讲。立群指出,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给人文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些对文学阅读和文学生活的普遍新期待也悄然到来。那么题来了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研究?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研究?伴随着这种题的认识,“疫情期间的文学研究”这一话题逐渐应运而生。立群详细讲述了疫情期间他现代文学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2019年底,随着疫情的爆发,他所在的疗养院实行封闭管理,他过着长期“隔离”的生活。我经历了许多复杂的情感,开始思考如何在可能面临的历史变迁和混乱中获得个体生活的稳定和安全,以及精神上的丰富和平静。此时,沉从文求变中求不变的思想,以及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抒情诗人的冯至在二战期间依靠诗学哲学寻找“不变的本质”的思想浮现于他的脑海中。在我看来,这些现代文学作家的探索,让我找到了两件求稳的宝藏。一个是千百年来没有改变的古老华夏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是寻常土地上一棵树的姿态和样子。小草的生长,小鸟的飞翔,蕴含着永恒的美。这场疫情也为世界每个国家、每个人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与休闲、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自然中寻求生命的滋养和乐趣提出了新的命题。带着这样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也找到了一条新的思想史和精神史路径。我开始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并转化为实践,从日常生活中,在自然和历史的三个永恒中发现生命的新力量,进入一种生命的沉思状态。2020年,随着疫情形势更加复杂,我也面临着更加深刻的困惑和焦虑。这一情节体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从而引发了在时空相隔的经典作品中寻找知己的更大愿望。此外,2020年以来的全自然和社会危机也迫使人们思考如何面对大变局和动荡的时代,应该用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来看待复杂的中国和世界,更进一步,如何说话以及如何做事。这些都促使我进一步回归经典阅读。于是在2020年,我写了《立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作为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哔哩哔哩等媒体上与更多的年轻人分享我的鲁迅作品阅读心得。2021年,撰写《立群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立群认为,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标志。首先,这是一部个人文学史。有吴晓东与洪子成对话中提到的“再现经典”的想法。其次,这部作品有意识地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立足于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对教学的反思。立群指出,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由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支撑的,但现在的文学史教育似乎离这些作家的作品越来越远,也因此远离文学,这也使得文学研究面临危机。此外,立群还参与了疫情期间王德厚《鲁迅研究笔记》立群评注版和儿童作家金波著作《昆虫印象》立群评注版的撰写,并撰写了立群评注。周版的《新认识》在兄弟研究、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等话题上产生了新的认识。
在立群看来,他早期研究中关注的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这两个人物始终表现出人性中的悖论,即巨变与稳定、创造力与保守、激情与温暖、粗暴。而在温柔、不平衡与平衡、无序与有序、冲突与和谐、崇高与平凡、生命的重量与轻盈之间徘徊,在永恒的和解与挣扎中形成永恒的迷茫。这样的划分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依然会存在。存在。正是通过疫情期间对现代文学的学习,让我对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有了新的认识。这些经典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和诠释,渗透到不同时代不同的现实,成为动荡中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晓东和洪子成提出的文学经典题不仅是过去的题,也是未来的题。我们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也决定了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三重性中,文学经典成为每个个体的生命支撑,也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生活的动力和目标。
立群的演讲让在场嘉宾感受到了文学和生活的力量。接下来,与吴晓东进行文学话题对话的洪子成老师向大家讲述了十几年前的谈话,并就一些题提出了自己的更新思考。洪子成首先回顾了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性”题的几次重要讨论,如2001年作家李拓与《北京日报》编辑李静的访谈《论“纯文学”》,以及《天涯海角》在海口的另一个例子。《》杂志发起了王晓明、韩少功、蔡湘等学者、作家参加的研讨会,旨在拓展文学的边界。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合法性”的研讨会。此外,北京大学吴晓东、何桂梅等老师还组织了“文学自主”学术论坛,利用韦伯等思想资源梳理文学审美自主的历史脉络,最终落实到现实题中。还有一些小对话,如蔡湘与王晓明、吴晓东与薛毅等的对话,构成了2000年至2010年文学话题的重要讨论。这些文学性讨论所针对的主要题是文学性的脱节。文学与社会史之间的矛盾、“纯文学”的无力、线性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弊端。针对这些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李欧梵主张将文学研究开放到文学的“合法性”和文学的边界等“非文学”题,如广告、产品手册等。也可以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吴晓东的演讲体现了他对文学性的坚持和深入探索,体现了他对“个性、偶然性”因素的重视,以及一种不同于线性历史叙事的“原创”文学史。从吴晓东此前出版的作品的标题来看,这样的倾向在《文学的命运》和《文学的诗灯》中也能看到。从这些讨论中,洪子成看到了一些观念上的差异,于是产生了与吴晓东就文学性、文学经典和阐释等题进行交流的想法。洪子成指出,他关心的题是文学是否真的面临危机,或者说判断文学是否处于“危机”的标准是否只是一个时代是否有伟大的作家。纵观文学史的叙事,当下的“危机”感是否总能在一定的时空距离后转变成可以回忆的“黄金时代”。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体系以及文学研究者研究思路的变化和分歧,都表现出更多的文学性思考。在与吴晓东的交谈中,洪子成深深感受到,对于吴晓东来说,“文学性”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一个需要不断补充的不确定范畴。吴晓东的这部新作是他二十多年文学研究的总结和巅峰之作。这也体现了他对文学性的信仰和复杂的看法、对理想文学叙事的追求以及文本分析的技巧。吴晓东一直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这些文学研究从细致的形式分析开始,最终遇到了政治,到达了历史和人的维度。这样的文本分析方法的存在,让文学研究者心中有尺,眼前有光。
洪子成的演讲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评论。它不仅有历史感,而且有理论上的提高,充满了个体生命的丰富感性。接下来,中山大学黄子平老师在线参加了本次研讨会。黄子平从洪子成与吴晓东的对话入手,指出对话中许多尖锐的题和回应,为探讨文学本质的张力开辟了空间。黄子平认为,当今时代,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无时无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无所不在。具体到吴晓东的文学研究语境中,或许可以分析出两个层面的“文学性”,一是作为信仰的文学性,二是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就“信仰”而言,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吴晓东在谈话中对文学性的坚持。当很多人似乎不再坚持的时候,这种坚持或许会被视为“痴人说梦”。或者是一种幻觉,一个乌托邦。吴晓东用了一些宗教性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种坚持,比如“安慰”二字,将文学视为心灵安息的地方。对此,谈话中一个非常精的说法是,“作为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你想相信什么,那可能就是文学”。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这种对文学的信仰。例如,神秘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指出,文学的“虚构性”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对现实生活有害。西蒙娜从神学角度否定文学,但她提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是追求一种“资本善”。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等待和专注。黄子平认为,这两种精神其实都与文学有关。信仰的文学性也让黄子平想起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中对宗教的论述“宗教中的苦难不仅是真实苦难的表现,而且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如它是一个没有精神活力的体系的精神。”接下来是人们熟悉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黄子平看来,用“文学”代替这里的“宗教”,或许是吴晓东在谈话中对自己信仰文学性的解释。当然,接下来要考虑的题是马克思所说的“天国”被驳斥后,“地”会怎样。马克思的观点是将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实和革命行动的批判,这也关系到文学如何回应时代要求、如何介入现实话题。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题。但无论如何,在吴晓东身上,作为信仰、安慰和乌托邦冲动的文学性始终存在。其次,在“方法”上,黄子平指出,试图用理论来界定文学性的结果只能是同义反复,即“文学性使文学成为文学”。这是坚决的立场。但这也是一个稍微苍白的定义。因此,真正的文学性是一个现实题,就是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使……成为文学”,这涉及到俄罗斯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等方法。在大学文学教育中,文学性的坚持和实践应转化为对学生审美情感的培养,即所谓的美育。这种文学情感和审美情感构成了文学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吴晓东提出的。生活经验中最微妙的存在,只有文学才能触及。黄子平最终用“旗帜”的诗意隐喻综合了“信仰”与“方法”的文学本质。它不仅是一种信仰的寄托和象征,
想了解更多关于理群、洪子诚、吴晓东等“再谈文学性”诗学、历史与人和对疫情的看法采访对话稿的题,请持续关注本站。